一个“美役人”的荒诞时刻
最近,一位来自河南南阳的小姑娘七七因街拍走红。视频中,七七素颜出镜,网友们赞她神似张柏芝,奉为神颜。基因是一种彩票,甚至可能是最大的彩票。一张美丽的脸,本身就足以让人趋之若鹜。
而对更多普通人来说,美丽是一件需要努力才能维持的事。伴随着颜值经济,“服美役”引发了很多争论。这个词语的命名以及持续流行,说明它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
如今,一个典型的“都市丽人”往往是这样的:
漂亮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饱满的嘴唇;
考究的穿搭;
光滑平整的肌肤;
苗条修长的身材;
良好的发质,丰满的发量;
拿得出手的日常化妆技巧;
手指脚趾指甲形状、颜色好看;
手肘膝盖等关节部位光滑细嫩;
漂亮的眼睛;
高挺的鼻梁;
饱满的嘴唇;
考究的穿搭;
光滑平整的肌肤;
苗条修长的身材;
良好的发质,丰满的发量;
拿得出手的日常化妆技巧;
手指脚趾指甲形状、颜色好看;
手肘膝盖等关节部位光滑细嫩;
展开全文
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需要花费巨大的心力与财力才能维持。“服美役”说出了很多女性共同的感受:如同劳役一般,为了维持美丽持续付出时间、精力与金钱。
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拒绝“服美役”。但这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拒绝到何种程度?真的能拒绝吗?我们想建立一种新的游戏,但我们的砖瓦太有限。这一切有可能从哪里得到突破?这篇文章是一个曾经的“美役”人的自白,她讲述了“美丽”的荒诞与复杂。
这里是“写在理论边上”专栏。对此前专栏文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阅读。
(本文中涉及的皮肤问题及就诊经历,仅为个人分享。每个人的肤质不同,不构成护肤建议。)
撰文|张婷
“服美役”的荒诞时刻
最近爆火的脱口秀演员小帕,谈及自己曾长期遭受容貌困扰,因自己体毛重、手大、脚大而引发焦虑。而实际上,她已经如此美丽。

脱口秀演员小帕。
当我们讨论“焦虑”,却发现它最终指向了“荒诞”。而这远非第一次。
我之前写到,即使在骨折期间,也希望自己尽量整洁、体面。我一直对外表比较敏感,后来发现有人可以对此毫不在意,顿时心生佩服。但就如同其他规训一样,敏感与否,有太多因素共同起作用。在意外表,不代表这个人更“软弱”(当然也不代表这个人更“美丽”)。现在很多家长有意识地不让孩子尤其是女儿频繁地照镜子,以此尽量减少她对外表的关注。我也一直以为这是由于自身性格以及成长环境造就的,直到很久之后,读到更多相关书籍,我才确认这不只是个私人问题——它的确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
我一直很注意护肤。青春期没长过痘,谁承想,工作多年后,开始长痘了。起初是脸颊泛红,后来会有灼烧及刺痒感。去三甲医院皮肤科,被确诊为玫瑰痤疮。之后做了很多过敏原测试,检查了激素:没有异常,也没有常见的过敏。最后,医生询问我的护肤习惯与护肤产品,说可能是由于过度护肤导致的。
医生开了盐酸米诺环素(玫满),同时建议刷酸治疗。于是我开始定期去医院刷酸,刷完水杨酸刷果酸。每次刷酸大概七八百元,不能报销,几个疗程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个过程里皮肤有了好转,但只要停止服药或者停止刷酸,痤疮就会复发。后来换了一家医院,医生又建议:皮肤敏感千万不能刷酸。长痘是皮肤屏障受损,而刷酸会导致屏障受损更严重。
护肤这件事,也跟世界上很多事一样,大家各说各话,各找各妈——充满未解之谜。

《服美役》
作者: [意]毛拉·甘奇塔诺
译者: 张亦非
版本:联合读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2月
某一个夜晚,脸颊又开始灼烧刺痒,我只能用冰袋降温。摁着冰袋,想想这些年自己兢兢业业地“护肤”:爽肤水,乳液,精华,面霜,早C晚A,玻色因,视黄醇,烟酰胺,胜肽……最后,反倒因为勤奋护肤而导致了玫瑰痤疮,真是荒诞啊。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再使用任何功效成分复杂的护肤品,只做最简单的保湿。但皮肤问题仍然反反复复。
当然,这又是一个资本的圈套:它制造问题,再解决问题,最后赚得盆满钵满。但如果到此为止,事情还没有那么复杂。
小帕在脱口秀段子里提及,她曾在经济拮据时斥巨资购买“黑绷带”面霜。拒绝的困难之处,或者说事情的微妙之处在于:它的气味、包装、质地都令她上头——即使你看透一切,你无法拒绝一切。因为你看透的一切,正是包围着你的一切。
在那个捂着冰袋的夜晚,我看着柜子上的“黑绷带”面霜,开始蠢蠢欲动:它主打修复,要不再试试?于是,我用完了剩下的半罐面霜。吊诡的是,我的皮肤在那段时间真的稳定了下来......
我同时也尝试了抗炎饮食,改善了作息——变量太多,其实很难确定是某一个改变或某一个产品的功劳。但我仍然没有摆脱护肤的“怪圈”。放弃护肤,或者精致护肤,都不容易。《服美役》一书的作者毛拉·甘奇塔诺曾呼吁,不要妖魔化护肤。她认为护肤代表一种仪式感,可以带来很多好的作用,重要的是,区分护肤到底是出于取悦自己还是取悦他人。但仔细想想,这真的成立吗?取悦自己,已然是当下最流行的营销语汇。多么贴心,你的预判被预判了。
对很多女性来说,这样进退两难的荒诞感实属“历史悠久”。
小时候,大家以瘦为美,班级里发育最早的女同学,甚至会被嘲笑,于是争相节食、减肥。瘦是最大的王道。《美貌的神话》一书中,作者娜奥米·沃尔夫引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在15岁至24岁的女性群体中,厌食症换算下来的年平均死亡率比所有其他死亡原因加起来还高出约12倍。厌食症已经是美国少女的最大杀手。
但长大后,女孩们发现,瘦还远远不够。“美”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该瘦的地方瘦,该胖的地方胖。单纯的瘦,成为一种新的“罪过”。主持人、译者陈鲁豫就曾因为瘦而饱受诟病。我们真的允许每个身体如其所是吗?
审美看似多元,但多元的美,也带来了多元的“束缚”。找到你自己的美,变成了新的魔咒。
美或者不美,都很难
“美丽”是一件极为占据时间、精力、金钱的事。如果你愿意,它几乎可以占据你所有的时间。
就说化妆这件事,学会化眼妆这一项就是个大工程。眼妆包括但不限于野生眉毛、内外眼线、自然的假睫毛、晕染适度的眼影、饱满精致的卧蚕......这都需要大量技巧学习以及日常实践,很可能要花费一个女孩三五年的时间。再比如,大众流行审美中的“漂亮指甲”,意味着一个女性有固定的美甲习惯,每隔一个月就要及时将新长出的指甲覆盖,重新补色或挫甲。这不仅考验时间精力,对指甲健康也会有损害。有一段时间我做指甲较为频繁,明显觉得自己的指甲更加脆弱了。
这只是最基础的日常保养。很多女性还会定期安排医美项目。对自己五官不满意的,甚至还要动刀解决。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因医美事故致残致死约1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因注射玻尿酸失明,因隆鼻导致皮肤溃烂,因抽脂命丧手术台......这都是我们有公共记忆,甚至反复出现的新闻事件。

《某种物质》电影剧照。
美役不仅束缚着最刻板的“男凝”视角下的女性,独具风格的美丽背后,几乎都意味着大量的精心打磨。即使是tomboy(假小子)式的呈现,也被认为需要精心打理的短发,讲究的中性穿搭,漂亮的五官,独特的气质。在社交媒体走红的“酷飒”女孩,甚至更要符合极致美丽与中性外表之间的反差。每一个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的女性,不管是线上互动,还是线下社交,都多少感到“美”的召唤。我们很少见到以展示“不美”为目的的图像,即使有,也会迅速被审美机制收编为一种新的“美”:素颜美,中性美,松弛美,慵懒美……一切的风格与个性,最终只是成为“美”的前缀——一种不同的形容词。
人类的复杂之处在于,我们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虽然常常被肢解),外表的美或丑,在一个动态的,鲜活的人身上会发生奇异的、崭新的化学反应。这样的理念让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美丽的。但,我们的预判再次被预判了。如果个体的美丽是流动的,那么它就是可变化的,它就是可演进的。这种“演进”带来新的问题:我们应该在何时停止?

《某种物质》电影剧照。
脱口秀演员王小利在段子里调侃“婚纱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勒得慌”。她是多么敏锐。为了拍摄婚纱照,我试过很多件婚纱,几乎所有的婚纱都是一种美丽酷刑。为了保持挺括,很多婚纱会在胸部或者腰部放置鱼骨塑形,有些在下摆还需要裙撑。即使没有支撑材料的婚纱,也往往有着复杂的绑带或是紧身的收腰设计。当我最终挑选出心仪的婚纱,肋骨已经被鱼骨戳得通红。几乎每一场婚礼背后,都需要“新娘”花费一整天甚至数天去试纱,之后还需要花费数小时试妆。
拒绝“服美役”,是否意味着拒绝婚纱,拒绝化妆,进而,拒绝一切仪式化的展演?我们想设计自己的“游戏”,我们的砖瓦却太有限。很多女性已经在实践不化妆,不买(少买)衣服,不留长发,不涂指甲油…… 但如此似乎变成了一个新的“竞赛”:头发没有最短,只有更短。对于那些喜欢化妆,喜欢穿新衣服,喜欢留长发的女性来说,“服美役”的指控是否构成了新的压力?最终,我们只能回到:每个人做自己能做的,选自己能选的。
当看到穿着婚纱、做好发型、画好妆容的自己,我发出惊叹:真美。但是如果考虑到为了这“真美”所付出的时间、精力与心力,这的确是一个性价比极低的“工程”。明星为外表所做的“投资”,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生产资料,最终转化为生产力。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对着镜子惊叹“真美”,最大的作用可能仅限于自我欣赏。

《某种物质》电影剧照。
但是,当我某天觉得自己“很好看”,的确会更有力量感。这又变得复杂起来。在现行的审美框架下,美貌具有“赋权”能力,或者说,美貌本身即是一种权力。网友们总是拥有精准的直觉——最近大家喜欢用“权威”来形容美丽:这是一张权威(美丽)的脸。
这不等于说拥有美貌没有坏处和陷阱。这一处境的困难之处在于,你知道“美貌”的权力感是从被凝视中获得的,但你还是会体会到那种力量,或多或少。
归根结底,如何区分这种力量是被建构的还是属于自己的?如何去区分,一个女性想画精致的妆容,穿精心搭配的服装,是因为她想取悦自己还是因为她想暴露在他者的目光之下时感受到力量?抑或者这两者已经合二为一。
这的确太难了。
新的凝视可能吗?
“服美役”的怪圈,其实与优绩主义如出一辙。
如同你可以变得“更成功”的许诺一样,你永远可以变得“更美丽”。新的风格出现,马上被审美机制收编。只要能进入生产体系,一切皆可成为新的生产资料。
这个调侃恰到好处地点破了“皇帝的新衣”之下的“新衣”。优绩主义的怪圈难以打破,正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困境。看到这个怪圈并不难,要摆脱它却不容易,作为个体,很难彻底地退出。但这不代表批判没有意义:这的确是一个变革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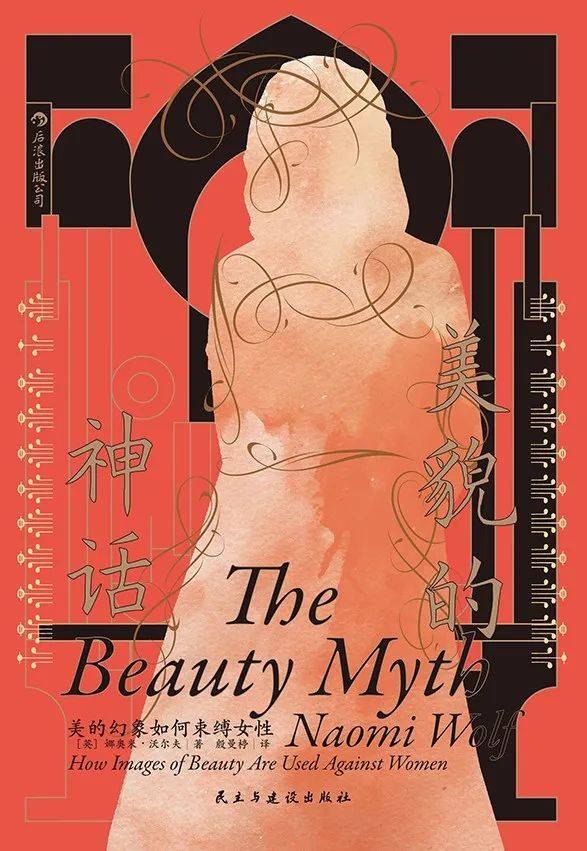
《美貌的神话》
作者: [英] 娜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
译者: 殷曼楟
版本:后浪/ 后浪智慧宫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年5月
木心古早时候写过一篇《论美貌》,他写道:美貌是一种表情,而这个表情的意思,就是爱。彼时读到,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演员这个职业,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被默认需要拥有一定程度的美貌。因为那是一个靠获取观众的爱而存活的职业。他们需要感染甚至操纵观众的情绪。而最好的武器,也最天然、最不易被察觉的武器,便是美貌。
《美貌的神话》一书的作者娜奥米·沃尔夫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论证:美貌是爱最大的敌人。她认为,在美貌的神话中,存在一种固有怀疑:美丽的女性不能相信能够仅凭她自身而被爱。当美貌消失时,爱会去往哪里?美貌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货币,却唯独不是我们自身。只要美貌与爱之间的强关联没有被解绑,“服美役”大概会一直存在下去。
但这种解绑并非不可能发生。这两年有几部好莱坞电影在选角时,特意选出了一些在传统意义上被认为“丑”的女演员做主角,因而备受攻击。也许制片方或者选角导演作出如此选择仅仅是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但或许会从这里撕开一个裂缝,改变人类的观看机制。最终我们会到达一个新的地方:好看与否,美丽与否,都没什么大不了的。谁知道呢?

《某种物质》电影剧照。
曾经提出男性凝视理论的哲学家劳拉·穆尔维,近年对她的理论进行过一次新的补充。她在其中谈及了“女性凝视”的可能性。通过探索神话、民间故事和女性侦探,她将女性的观察方式与好奇心联系起来:“(这种观看是)对知识的渴望、对用心灵之眼去看的渴望。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去性别化,是对凝视中的欲望元素的压抑。另一方面,好奇心提供了一个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刻:去反思、解读,通过陌生化的视角去看待已然被陌生化的事物。”
电影业,也曾经是一个被男性统治的行业,他们曾主宰着其中的权力与审美。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正在拍摄、创作、制作电影。也许这些新的女性电影创作者们会为影视行业创造出一种新的观看机制。
或许在未来,人类能够迎来这样的一天:我们打量彼此的目光,不再首先落在“好看与否”。我们的观看机制将不再由美貌来牵引,而是由善意的好奇心来牵引。
到那时,美貌与爱之间的纠缠或许会被打破。那么取而代之的“第一眼”,会是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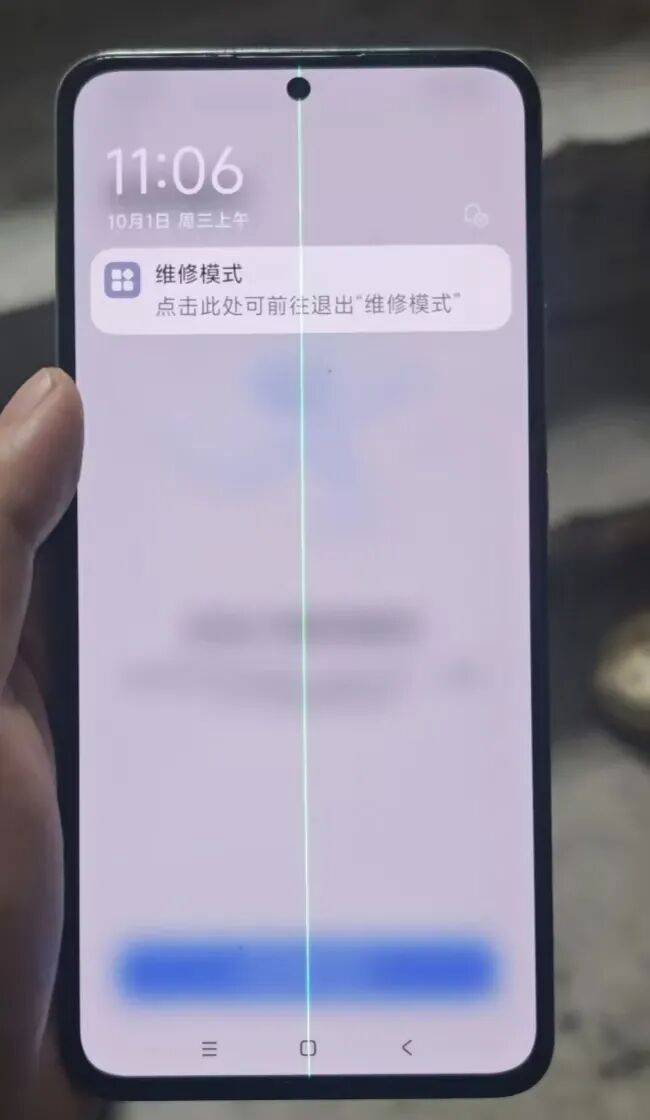


评论